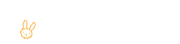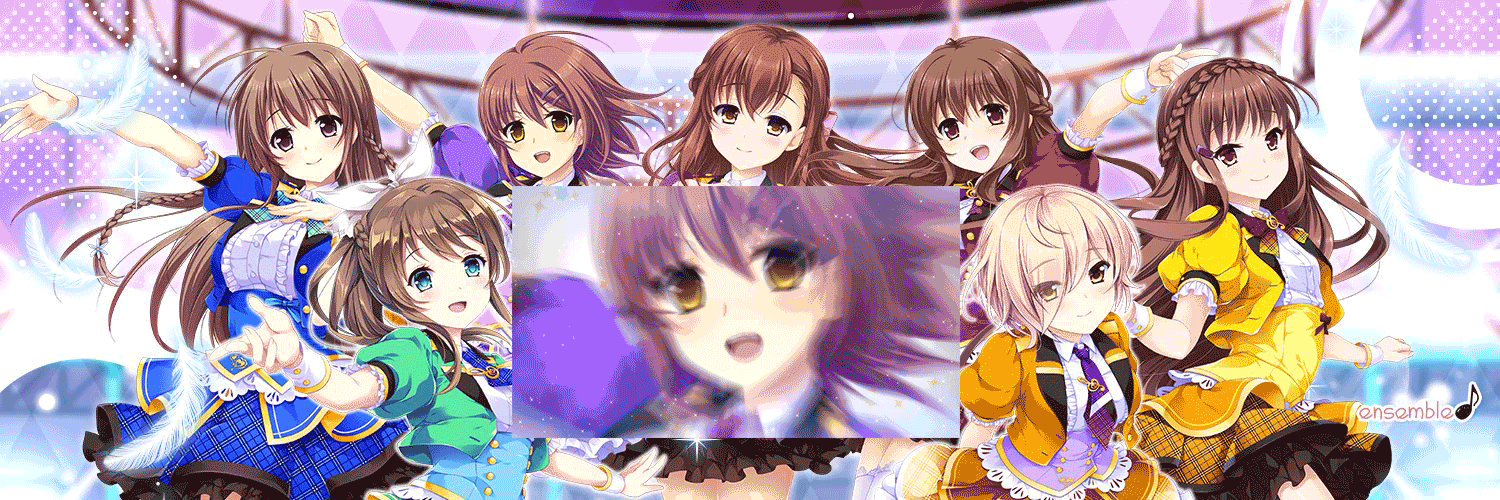|
回答“人是什么?”的答案千奇百怪,柏拉图讲“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根据他的这个答案,有人把只鸡拔了毛,拿给柏拉图看,以此耻笑他。回答“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必须小心谨慎。空间上就有无数个“中国”。假设一个旅行者走进了北京的琉璃厂,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于是,连四川湖南方面,大吃辣椒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时间上也有无数个中国,要是活在宋代,你会感叹中国“重文轻武”的不堪一击,而要是不小心到汉代,甚至先秦,你会发觉许多读书人其实都是那么“孔武有力”,任侠放荡,可以杀了仇人后提了脑袋在大街上从容穿行。因此,从时空上看,中国便都是“谜一样的国度”。
正如辜鸿铭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能够勾画出中国人的内在本质。”因此,任何人都无法用一句话回答“中国是什么”。 但我们可以回答“中国不是什么”。要界定什么是男人,你可以回答“不是女人的正常人都是男人”(这样就排除了阴阳人和宦官)用现代西方人的视角来为中国定位,是一个现成而且方便的办法。 “谁更文明:不争以为争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习惯把上公交车不排队,随地吐痰之类看做中国人有“私心”无公德的罪状,是不够“文明”的现象。且不说一个中国乡下的农民是否需要找到一个路边的痰盂再吐痰,习惯了曼切斯特和纽约生活方式的英国绅士和美国暴发户,当然无法理解,这些农民或者农民后人,被裹挟到城市中来时的生活不适。早期外国人对中国农民“不文明”的生活方式的鄙视,正如今天被很多城里人鄙视的农民工,问题的前提是,是谁让他们离开农村,破坏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在追赶西式文明中遭受的屈辱,与农民工在“农转非”过程中遭受的屈辱,可谓异曲同工,既是学生也是奴隶,必须接受“老师”的标准和谩骂,绝无争辩的权利。 其实,真正中国人崇尚的美德足以让很多西方人汗颜。测试一个人真实素质的办法,是去研究他在饥寒交迫而又浑身湿透时的表现。如果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就“温暖他,烤干他,喂饱他,这样造就出一个天使”。英国人常说:“碰到一个被剥夺了一顿饭的英国人,如同碰到一头被抢走幼子的母熊,两者同样危险。”不难看出,盎格鲁—撒克逊人懂得,尽管他们拥有值得吹嘘的文明,但仍然受制于他们的肚子。“文明者”的兽性并不比“不文明者”要少。 明恩溥笔下的中国人却拥有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的特质,他曾经记录过一次中国人的宴会:“大约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走了几英里路,他们是来出席一次宴会的,但却让他们失望又受折磨。他们原本指望十点钟左右坐下吃饭,这是他们中许多人这天的头一顿饭,但由于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况,他们只好站在一旁做招待,受招待的人数比他们还多。”明恩溥感叹道:“受招待的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从容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特色,比起我们来要先进许多。”他又将之与大不列颠的子民们比较道:“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居民,我们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一定会怒容满面一整天,在下午三点最后一轮宴席上坐下来之前,就会对他们的遭遇抱怨个不停,不住地怒骂。他们会一致通过一个激烈的决议,并且“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信,信中包含五个‘Now,Sirs’(现在,先生们)”这样的激愤之辞。“虽然明恩溥认定没有哪个西方人能有这种“度量”,显然更多中国人认为这恰好是中国国民性的“懦弱”之处。对个人权利的争夺,是尚“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然传统,而中国人的传统则是“尚让”。“争”可以是无原则的“争”,让却并非无原则的“让”。“争”是一场超越了边界的战争,从一家人为遗产的争讼开始,到残酷的商业竞争,直至军事入侵与种族灭绝,西方人在数百年时间里统治了全世界,灭亡了玛雅文明、印第安文明,东方的各大文明几乎都被其奴役过。这表面上辉煌的战绩,其实也并不一帆风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宾格勒写出《西方的没落》一书,整个欧洲陷入坟墓一般的绝望与死寂。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战前还对欧洲物质文明歌功颂德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下陷入迷茫。梁启超由此认为欧洲的物质文明纵然好,还是得配上中国的精神文明,西方文明好比四肢发达,而头脑不灵,需要借助中国文明的脑袋才能“死而复生”。直至今日,西方依然困扰于“争”的哲学中,愈争则敌手愈多,“文明的冲突”成为永无休止的战争。 中国人的头脑却不是“尚争”,而是“尚让”,是“不争以为争”。中国人的“威服四夷”,其实并非武装占领,而只需要你象征性的臣服于我,进贡些土特产,天朝却报之以远超其价格的厚礼。中国人讲:“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你主动来跟我学习,我当然欢迎,我却绝对不主动强迫你改宗我的文化。此点,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动辄和人强行"搭讪"的作风截然相反。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时候,在陪都重庆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的月饼店,名气很大,每到中秋时候,远近的人都要到它那里去买月饼.甚至昆明的达官显贵,也会专程坐飞机去他那买.但到中秋前几天,老板却关门打烊了.人们问他,为何生意这么好,却不卖了,他说,这整条街上,有十几家月饼店,和自家都沾亲带故,关系不错.如果你们都不买他们的月饼,只买我的月饼,他们的日子就会很惨,甚至有可能因此倒闭,家人流离失所,要是某天我也落到这步田地,又于心何忍?这种"同情"的感觉,正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都是有恻隐之心的,没有恻隐之心的是禽兽不是人.现在看来,那"过去的"、"老年的"中国,倒是像个童心未泯的孩子,而"今天的"、"年轻的"中国,反而在欲望的沟壑里被填平了.政治的浩劫过后,继之而起的是商品大潮的冲击.这个冲击比政治的席卷来得彻底.前者多属被迫,好比强暴,后者纯属自愿,好比苟合.强暴在法律上可以平反和定罪,苟合却合法且多被提倡.此刻,面对汹涌的物欲之潮,我们怀念童年,渴望童心,正是无声的呐喊. 中国人不是钢笔 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这个早期汉学家的视角,老外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看麦兜系列电影,知道“春田花花幼儿园”里,师资优良,是老外教国语。让老外教中国人国语,大至跟让老外理解中国人的头脑一样富有喜感。 西方有这么一个滑稽的故事,说是有个旅行者在某地看到一个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很老的老人,很伤心地在哭。这个少见的情况使这个旅行者感到奇怪,他就停下脚步,问这个老人哭什么,老人的回答令他惊讶不已,说他父亲刚刚鞭打了他一顿! “你父亲在哪里?”“在那里。”老人回答说。旅行者骑着马朝着那个方向走了一段,发现的确有个更老的老人,胡子更长更白。“那个人是你儿子吗?”旅行者问。 “是我儿子。” “你打了他?” “打了他。” “为什么打他?” “因为他不尊敬爷爷,他下次要是再那样的话,我还要打他!”可是,如果把这个故事搬到中国人的情景之中,就不滑稽了。 明恩溥曾经读到过这样一篇报到:一个中国人拥有一些稀罕的古币,有个外国人想买。这个外国人担心钱主不卖——一个人有样东西,另一个人想要时,中国人就是这样做的——发现古币的那位中间人就建议外国人送点外国糖果之类的小礼品给钱主的叔叔,这种间接施加的压力,会使钱主不得不把古币卖掉。 这则报到让明恩溥大跌眼镜,他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如此的 “孝弟”关系与西方人的“个性自由”显然冲突。没有一个中国人是为自己活的,正如没有一个美国人不是为自己活的。“家”的观念在西人那里是淡漠的。我曾经有一个在耶鲁念书的日裔美国人同学,他到北大来交流一年。他告诉我,自己18岁就独立出来打工,直到读大学,父亲与母亲离异再娶,与家人更无多联系,他偶尔提到“my father and his wife ”,也仿佛武陵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茫然辽远。他自己从刚长胡子到目前为止的N段感情,最长不过四个月。在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咏叹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看来,更加不可思议。 谈到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中国人是不会孤独的。在家中,稳定的人伦关系让我们获得温暖与秩序感。尽管明恩溥依据美国人的功利心,断言“孝道”的存在基于半是恐惧的心态——恐怕自己的不孝顺成为将来子女效仿的榜样,却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真诚与执着。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父母既是创造者,亦是永远回归的港湾。“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直至今日,亦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基础。 仅次于家庭成员之间责任的,便是邻居之间的相互责任。“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是否亲戚并不重要。“孟母三迁”的故事早就告诉我们,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邻居关系重大。而一个西方人,根据主宰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共和观念,对他来说,同谁做邻居都无关紧要,假如他住在城市里,他可能住了一年还不知道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一只鹅为什么还要选择哪只鹅做自己的邻居呢? 根据明恩溥的观察,中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的《京报》曾报到,中部某省的巡抚报告说,他处理了一件弑父母的案子,处理结果是推倒这个罪犯所有邻居的房屋,因为他们玩忽职守,没有用好的道德教化去改造这个罪犯。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完全合情合理。 当然,今天,城里人都已经住进了“钢筋水泥堡垒”,“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更不会出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怪事。今天的中国人,正步调一致的迈进城市,选择生活在这石头做的森林和监狱中,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小格子里渴望着海市蜃楼般的田园牧歌与天伦之乐。 传统的中国人是喜欢管闲事的,邻居的事绝对不是“旁人的事”。当今的中国正在改变,一幢幢钢筋水泥建筑高耸入云,一边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一边疏远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城市的生活成为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孤独。 我家所住的商业小区,底楼的很多住户不顾安全规定,擅自挖地下室,甚至挖动整个楼层的地圈梁,不过是为了一家人多一个通风不良的“休闲室”。面对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整个小区几百家住户竟然视若无睹。我问起一个二楼的住户,他楼下那位天天挖地,会不会危害到自身的安全?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没有啊,哪里有?哪里在挖?” 若是在农村,有人修房子挖了你家祖坟,断了你家地基,不仅邻居,全村人都会一拥而上,自然有一个“公意”主持正义。即使是城市,若是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院子,居委会大妈,热心肠大婶儿,孔武有力的知识青年,面对此种“缺德”事儿,定然不会袖手旁观。今天,“往事都已如烟”,飞速现代化的同时,人与人间却更像一具具兵马俑_冷冰冰的陶制僵尸。一个并不习惯争讼的国度,又丧失了它耐以维系社会秩序与温情的人伦道德,情何以堪? 试图让一个西方人理解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就像一条原本笔直的路接上一条“曲径”,必定无法通幽,却十有八九会出车祸。 明恩溥通中国语言,穿中国服饰,在中国生活多年,号称研究中国最早的汉学家,这个早期中国专家认为“中国人的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一样)经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风俗上的不习惯,在老外们看来,正是“虚伪的客套”,然而,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把你当作贵客来招待,并不仅仅想让你吃饱,而是要曲折和委婉的表达自己的好意。在脑子一根筋的老外看来,谁给自己面包,怎样给自己面包,统统没有意义,只是虚伪的客套。只有面包填饱肚子本身才靠谱。 辜鸿铭曾经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批判明恩溥对中国人素质的一个评价,即中国人“漠视精确”。明恩溥举例说:一个询问法律事务的中国人告诉明恩溥,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的叙述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问了他,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进一步交谈之后,才明白他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明恩溥完全崩溃掉,他抗议道:“你就没想到过如今你已然住在城里了吗?”中国人很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显然,那个中国人很有可能对明恩溥说他的“家”在农村,正是“根”在农村,是“come from the countryside”。而明恩溥用“Where is your house?”来理解中国人“家”的概念,自然南辕北辙。今天,一个在北京、上海打工的年轻人,如果被人问起:“你的家在哪里”,毫无疑问,他们绝对不会说出自己租住房的地址,而会说出自己长大的地方,那里有自己的亲人和家。 辜鸿铭把这种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心理解释为“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或智力一样,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 实际上,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硬笔是写不出真正的书法的,即使庞中华,也失败了。 除了“漠视精确”,明恩溥还归纳了中国人拐弯抹角、天性误解等种种“另类”,这一切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横亘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中国,人们关心的一切事情中,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情便是钱。明恩溥调侃道:“如果外国人付钱买东西(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常常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就是一种“军需物资”。“你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但汉语里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简单地说。“干活,拿钱。”他心目中的主要观念是挣钱,根本没有“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给外国人干点什么,他希望马上拿钱,以便“吃饭”,仿佛假如不是偶然碰上这个外国人的活,他就没饭吃了! 由此,明恩溥把中国人理解成“见钱眼开”的市侩。如果说,这世界上一个人永远无法理解另一个人,那么一个世界不能理解另一个世界也就理所当然的。中国是无法被不中国理解的,要真正理解中国,必须自己先变得中国。《南京条约》里,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的“城厢”居住。关于“城”没有异义,什么是“厢”?中国人认为是靠近城的地区,比如农村,英国人却坚持认为是城市本身,双方争端乃至战争由此而起。其实西方人并不缺乏了解中国的能力,而是缺乏这种心态。假设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同学,想要追求一个北大的女生,然而他不是北大的学生。于是他找到该女生的课程表,凡是她去的,他也去。凡是她不去的,他便不去。但他还是未能如愿。于是他自我解嘲道:“因为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但很有可能,这个女生本来就有男朋友,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俗看来,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当然也不会事先过问。 1840年前后,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观感便大至如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于是奇怪中国人为何不接受,而由于中国人固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却头头是道的自我辩护,便是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了。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是要和“国际接轨”,全球化就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大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然而,和一个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人在一起,除了同床异梦,还有什么呢? |
|
|
沙发#
发布于:2009-08-09 13:25
我只想说,空行太多了啊
看着吃力 |
|
|
|
2楼#
发布于:2009-08-09 13:29
好多字……
其实只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够了…… 人反正都要死……那活着是为了什么?…… |
|
|
|
3楼#
发布于:2009-08-09 13:38
回 2楼(殛嘵·劍_殘) 的帖子
活着是为了吃饭睡觉 |
|
|
4楼#
发布于:2009-08-09 13:38
好长。。。专业问题免疫
|
|
|
5楼#
发布于:2009-08-09 13:42
中国不是东方里的红美玲嘛 =w=
|
|
|
6楼#
发布于:2009-08-09 13:47
为啥搞出这么个问题来啊。。。。。
|
|
|
7楼#
发布于:2009-08-09 13:48
深奥的问题~~
|
|
|
|
8楼#
发布于:2009-08-09 14:08
人其实都一样……中国人也就那样……
|
|
|
9楼#
发布于:2009-08-09 14:34
好长,留着晚上慢慢看
|
|
|
|
10楼#
发布于:2009-08-09 21:57
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啊。。。
|
|
|
|
11楼#
发布于:2009-08-10 00:22
3千年的历史,是辉煌也是枷锁。
|
|
|
12楼#
发布于:2009-08-10 00:41
不管怎么争都是物质和意识的分歧问题,没意义
|
|
|